

在中国,城市规划是一个热门专业。但在英国,这个专业并不热门,为什么?
因为城市规划是增长的敌人:规划的名声不大好,每当新的领导者上任,为了让经济增长,首先会削减规划。因此,西方的城市规划,与中国截然不同。
中国的市长就任后,会大兴土木,做一番规划。大家对比一下东欧,就知道,在社会主义经济垮台后,规划师都无所事事——因为计划经济都不要了,还要什么规划呢?在中国,事实上是在改革开放、引入市场经济后,规划的地位得到了高度抬升。
为
什么中国的城市规划这么热门?我想有三个解释。第一,在中国,规划适应了市场;第二,规划能解决市场化带来的很多问题,如环境问题、社会不公正问题;第
三,规划其实创造了一个增长的话语。通过创造增长的话语,它强调了国家的权力,成为国家管制的一种手段,从而也提高了规划自身的地位。这就是我想谈到的三
点。
回顾中国改革开放前的规划
我想先回顾一下中国的规划。其实,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规划的国家之一。城市的建制有一定规制,《周礼》就有记载。但实际建设又因地制宜,比如引入所谓风水,以及建造时要负阴抱阳等。因此,城市的选址,也就符合自然地理条件。
在此条件下,对中国城市进行研究,意义在于“wall city”,即有城墙的城市。在帝国时代,城市是统治的中心,比如衙门。这里是上海的县城图。

租界建设时期
真
正现代意义的城市规划,起源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的租界建设。当时为建造租界,规定了土地细则,从而逐步延伸出城市建设的规制。当然,在此时期,城市
是分隔的,分成中国传统的城市部分和租借地部分。青岛这样完全的半殖民地城市,就显现了宗主国德国的风格,而哈尔滨就体现了俄罗斯的风格。
很
有意思的是,1927年,上海做了一个“大上海计划”,理念十分先进,要在江湾建立“新市民中心”,要将分裂的租界和华府联合起来,变成一个城市的中心。
在这个计划中,有市政厅、博物馆、图书馆、医院等,都是为市民服务的建筑。整个计划因抗日战争爆发而未得实施。现在,要寻找当时“市民性”的建筑,还是很
困难的。比如,现在的体育学院中间,有一座建筑就是当时规划中的市政厅,现在作为中西合璧式的图书馆。在社会主义时期,市政厅在某单位的围墙之内,但它本
该是一个开放的、具有服务性质的市民中心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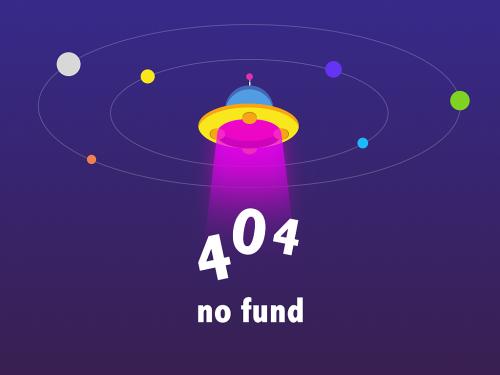
1927
年在南京也有一个“首都计划”,设想在紫金山南麓建设一个中央行政中心。当时的设想十分宏伟,要在明故宫遗址上,建设一个商业中心。因明故宫离城市较近、
土地平坦、发展较成熟,如果把该地设置成商业中心,会取得很高的土地收益回报,从而支持新的中央行政的建设。但当时,因为国民党两个派系的争执,这个计划
没能实施。
1946—1949年,上海区域规划编制了三轮,共有三
稿方案(这本书已被上海规划院重新编辑出版)。当时的规划理念非常之新。1940年的“大伦敦规划”,强调有机疏散、强调邻里建设,而上海这些规划中,就
提出要在市域里建设新式居民区,当时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理念。所以,当时中国的规划水平,可以说和世界水平比肩平齐。
把
规划师作为一种职业,这缘于现代中国的形成。它继承了中国对城市的传统认识,有着强烈的建筑和工程传统,以空间构建为工作核心,蓝图式的规划风格始终得以
保持。城市规划把城市看作放大的建筑,广义上,是当作一种人居环境。在塑造人居环境过程中,规划师始终是能动的,坚信能通过规划建设实现强国富民,通过整
体设计可以对城市进行通盘规划。然而,由于受到战乱、经济波动的影响,规划起的作用非常有限。
当时,规划师呼吁建立新中心,政治家却踟蹰犹豫。或因党派纷争,或因财力有限,这些宏伟的规划都未得以实现。而现在,情况恰恰相反,规划师对建造“新中心”十分谨慎,而政治家却在说,自己要向东或向西,建设新的中心,进而让规划师重新布局。
由此,当时的规划来自学习西方,通过现代化、建设新城市,来实现社会理想。可惜在当时都以失败告终。
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
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,这段时期的规划,有巨变也有不变。变的是国家具备了强有力的实力,不变的是现代化的理想。只不过,现代化是通过工业化实现,强大国家实力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,而不是城市化、市政建设。
这一时期在国家层面,国家对产业布局的能力空前强大。对生产的项目,通过审批,可在全国范围内布局。在冷战高峰时期,为提高工业生产能力,实行了所谓“三线建设”。
而
在城市建设方面,则借鉴了苏联的卫星工业城镇建设。实际上,苏联的经验受到有机疏散、花园城市等西方规划理念的影响。在北京,有“十大边缘区”;而
1959年的上海,也设想建设新城,但受到1946—1949前一版规划的影响。有意思的是,解放后,陈毅市长采纳了国民党时期的上海城市规划,并没有对
它全盘推翻。
社会主义城市最吸引人的城市特色,是城市外围的“工人
新村”,如上海的曹杨新村。当时,曹杨新村有2.5万户。我的外婆1990年代住曹杨新村,是使用马桶的,可见曹杨新村当时虽然建设标准相对不高,但很先
进。当时曹杨新村的房屋,是赠送给工业界的劳动模范人士的。其模式受到苏联影响,即所谓的“super
block”(大邻里街坊)。它很适合苏联的严寒地区,居住的楼宇沿街坊布局。
当时的建筑还是不错的,如北京的百万庄居住区,是中央机关单位辐射区之一。不过,百万庄也在近期的拆迁计划当中。改革开放后的大规模居住区,还有北京的方庄。
这
种大规模居住区的建设仅是一部分。社会主义城市建设,另一个受关注的现象,是城市的形象,即所谓斯大林之建树,或说社会主义的宏伟形象——宏伟的社会主义
城市。比如北京展览馆,当初工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,把几吨重的红五星搬到建筑顶上,但在唐山大地震时,红五星掉了下来,后来被换成了塑料。
当
时“梁陈方案”设想,要建设新中心,但最终没有这样做。我可以理解政府的意图,第一,想维持旧城;第二,因为国家财力确实有限,建设新中心的决心难下。城
市建设实际是非生产性的投资,并没有资金的循环体制,所以建设新中心的决心难下。政府机关被设置在长安街两旁;大量居住区没有规划,而是见缝插针。北京很
多四合院,在解放后逐步走向衰败。
但是,大规模的城市建设,确实是不存在的。社会主义城市和大家想像的不一样。社会主义的国家虽然是强有力的,但它的城市建设并非通盘规划、通盘建设。社会主义城市不需要规划,也不能规划。原因是,社会主义城市是高度分割的。
分
割首先是垂直的分割,就是单位体、单位制。规划对单位内部的用地,是无法进行管制的,规划只是国民经济的具体化,是计划经济下位的选址规划(或工业选址规
划),量大面广的住宅开发,实际是单位制内部的计划,不是城市规划可以直接干预的。所以,这时的城市规划,并不像在西方资本主义城市那样是社会集体消费的
产物。
另外,规划的影响力也非常有限。对乡村地区,实际上没有规划,规划止于城乡边界(state domain),对农村是不管的。
之所以建新中心决心难下,也是因为基础设施负担大,缺少投资机制。
实
际上,这时的规划,不是在公共领域的对话(public domain),规划是一个国家、单位体制内的规划,是在体制内部的(state
domain)。所以,单位的存在,并未使规划能直接深入单位内部。在这样一种特殊体制下,公共利益无需界定,规划实际上不是一个需要讨价还价来协调控制
的手段。
中国的“规划体系”
向西方人介绍中国城市规划时,他们觉得非常难理解。对不熟悉中国规划情况的人来说,要了解中国规划体系,简直是盲人摸象。因为存在三种规划:住建部的法定城市规划体系、国土资源部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,以及发改委系统的“五年计划”和发展纲要。
城
市规划存在两层:总体规划是城市发展的定位以及土地利用的总体布局;下放到下位是详细规划。实际上,城市规划真正的得意之时,是改革开放以后,1990年
实行的城市规划法,确定了“一书两证”(现在的所谓一书三证),建立了发展控制机制——在西方规划里面,其核心就是develope control。
当
时,在城市的总体规划之上,还有城镇体系规划,所谓城市的结构、功能、布局等等。但实际上,城市规划对城市的规模没有控制能力,虽然可以通过项目选址来间
接控制。所以,即便在社会主义时期,所谓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、积极发展小城镇、合理发展中等城市,这种规模控制,实际上没有实施能力,除非把它落实到公共
政策中。
总而言之,中国的城市之路,和英国非常接近,实际上是建立
在自由裁量的、规划许可证基础上的规划体系。也就是说,规划师看规划图,面对规划的申请,决定批准还是不批准。它决定批准还是不批准呢,要到实地考察,根
据对规划的理解和对规划申请的认识,决定是否批准规划。即“规划许可证”和“法定规划”本身的联系,要依照规划的“实地情形”的考量——这在市场体制下,
实际是一种政治利益问题,也是规划体系中薄弱的一环。
所以,在改革开放后,市场经济迅速发展,就出现了规划失控。
我
们老说规划失控的一些具体原因,如:总图不够细致,需要建立控制性的详细规划,搞得更详细一点,建立一套指标体系;或者,规划控制的范围不够,于是把规划
全覆盖,扩展到乡村地区;或者,控制不够明确,那我们就设定蓝线、红线等;或者,规划缺乏法律地位,在上海、深圳就实施了一些法定图则的尝试,等等。
这
些做法都是想加强中国规划的控制能力,但这是很困难的。因为,中国的规划体系,实际上是一种“发展型规划”,或者是我所说的这种“为增长而规划”,而不是
一种控制型的规划。它实际上继承了计划体制下“资源配置”的功能,缺少“利益协调”的功能。在向市场经济转化的时候,这个“资源配置”的功能不仅并未消
失,还被试图进取的地方政府所俘获,成为其配置资源的一种手段。
相比之下,英国是规划许可证制度,其中有个很有意思的特点,就是说,我发放许可证,对你批还是不批,可以讨价还价,即要求开发商为社会做贡献,要贡献个小学、图书馆,等等。这个市政贡献,就是所谓规划得益(planning gain)。
那
中国的规划得益去了哪里呢?实际上,我觉得它积淀在土地的出让金上,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一部分。随着土地出让的规范化,“招拍挂”机制的应用,中国的
planning gain,相对来说比较透明。当然,也有腐败等问题,毕竟这个体系本身,还是比较透明的。
但
是,规划的收益以金钱形式存在,并未成为一种福利供给,往往作为土地增值性投资,成为“增长机器”。所以,社区看不到这些钱,看不到相应的规划得益,从而
对规划的政治参与兴趣,相对较弱。当然,在居住小区中,如果有块绿地要占掉、要开发的话,小区居民会反对,因为这时居民能看到规划得益——如果不让规划,
绿地会被保留,绿地本身就是规划得益。而多数土地出让形式,其收益不会直接被社区居民利用,居民既然看不到,便也不会被动员起来,对得益进行讨价还价。也
正因此,规划不会为发展制造障碍,没有成为增长的敌人。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。
从规划的法定体系来说,从1990版开始,规划法建立了一个“发展控制”的程序,但九十年代主要的趋势是分权,在这个分配制下,把地方政府发展成型。所以这个“发展控制”程序,与当时的城市发展体制不一致,规划中的控制,往往没有想象的那样容易实施。
2008
年后,规划法才扩展到乡村地区,成为城乡规划法。在那个时候,可以说是迟到的规划法。因为,住建部管理下的城乡规划体系,有两大块东西没有得到控制:第一
是土地,土地是由国土资源部发放指标的形式控制,不需要在图上画很多块,实际上只要一个指标;另一块,是所谓资金和立项体系,它仍掌控在发改委的手上,而
发改委也把其计划体系逐渐空间化,成为所谓五年的空间规划。
当然,因为经济建设需要,城市规划学科大力发展,成为一级学科,规划也显而易见成为一种社会风格的蓝图,或者是领导的喜好——至少城市规划展览馆非常重要,展现宏大的城市发展蓝图。
回顾2000年以来,规划和政治体制的变化,实际上,西方学者一直讲到的是城市企业主义(urban entrepreneurialism)。
urban
entrepreneurialism是怎么产生的呢?西方的解释是,生产经济活动,由福特制向后福特制演变,转向灵活生产。所以资本流动加速,之后政府
要吸引投资,所以出现了竞争,从福利国家转向竞争性的政府,城市变为工地,成为企业化。也有很多在西方的中国学者,解释中国城市发展时,用这个urban
entrepreneurialism。
从这个角度看,中国的体制是怎样形成的呢?它是世界工厂模式下的城市发展,是城市的企业化建立的土地财政,就是地方政府通过人家出让土地吸引资本,而资本的到来自然吸引到劳动力。
这种模式有两个问题。第一,这里的劳动力,不是市民,没有发言权,不存在市民权,出现了所谓社会断裂和居住分异的争议;同时,大规模扩张土地,导致空间破碎,城市建设就像建设工厂一样,真正的城市没有得到繁盛的建设,或者说,没有形成实体意义上的城市。
城市规划起到了增加土地财政和税收、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。地方政府对城市规划非常重视。实际上,大家都知道,真正的总规划师是一把手——虽说请了规划师来看,让一两个月之内拿出规划方案,但实际幕后的总规划师,是站在后一排里的某一位。
[作者系伦敦大学学院(ucl)巴特雷特规划系讲座教授。本文整理自作者在同济大学的讲座分享,未经作者本人审订]